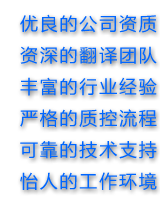屠岸:从事翻译是对缪斯的崇拜
前不久,著名翻译家、诗人屠岸刚刚过了90寿辰。没有张罗庆祝,没有到外面办酒席,只是在家里搞了一次家庭聚餐,三个子女及外孙女、重外孙女都来了,四代同堂其乐融融。屠岸吃了一点长寿面,就算是为自己庆祝了。
虽然年事已高,但屠岸的气色仍很好。回想几十年前的往事,他的记忆仍然清晰。说起自己这一代翻译家取得的成就,老人谦和而真诚地说:“我们从事翻译,不是为了谋生、解决生计,而是对缪斯的崇拜、对诗歌的奉献,是生命中的一种事业。”
译莎翁 只为悼念亡友
屠岸的书房四壁陈列书架,触目皆是中外诗选。他的书桌上放有去年的新版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》,这本诗集译成中文已有60多年。提起翻译诗集的往事,老人说:“我在上海交大求学时,跟我最好的同学叫张志镳。1943年他到了重庆,我送他上路。抗战胜利后,他回到上海,却得了严重的肺结核。”他动情地说,后来好友病情恶化,年仅26岁就英年早逝。
英国大诗人弥尔顿写过一首名诗《力悉达斯》悼念大学同学,屠岸也想写一首诗悼念亡友,又觉得自己的才华和功力不够,于是就转而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。“这部诗集大部分诗作都是莎士比亚送给一个朋友的,我就借花献佛,翻译过来送给张志镳。”他说,1950年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》初版,扉页上有一题词:“译献已故的金鹿火同志”,金鹿火即亡友姓名最后一个字“镳”的分解。这个秘密只有屠岸自己知道。
1950年,屠岸参与创办《戏曲报》,到胡风家去约稿,胡风对戏曲不熟,问屠岸最近忙啥,他就说在翻译十四行诗。“当时我觉得出版不合时宜,解放之初社会上革命气氛很浓,跟莎士比亚诗的浪漫气息有点格格不入。我对胡风说译莎翁诗只能作为资料保存。”可是胡风却告诉他,这些诗作是影响人类灵魂的作品,对今天的读者有用,对明天的读者也有用。在胡风的鼓励下,诗集很快得以出版,初版印了两千册,博得好评。
国内翻译欧洲十四行诗,卞之琳是先行者之一。1964年,屠岸对自己的译本做了修订,并写了译后记,送给卞之琳审阅。时值“文革”前夕,出版诗集已不可能,卞之琳就将译稿放在自己家里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卞之琳告诉屠岸,他在“文革”中虽被抄家,但译稿仍保存完好,这令屠岸感激不已。此后,这本诗集曾多次出版,每次出版前,屠岸都会认真修订。
诵济慈 获得生的勇气
屠岸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曾影响了很多人,即使是在十年浩劫期间,也有手抄本悄悄在民间流传。对屠岸来说,在五七干校劳动时,每当感到苦闷时,他就背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济慈的《夜莺颂》《希腊古瓮颂》《秋颂》等诗作。济慈是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,“我为什么喜欢他的诗,因为他用美来对抗恶。”屠岸说,那时济慈的诗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,使他获得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。
早在上世纪40年代,屠岸就开始翻译济慈的诗作,但之后中断了数十年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,他才花了三年时间译成《济慈诗选》。屠岸曾两度游历伦敦济慈故居,还去过济慈的墓地,并把译本郑重地赠给故居管理处。他还写过一首诗《济慈墓畔的沉思》,诗中写道:
你所铸造的、所有的不朽之诗
存留在“真”的心扉,“美”的灵府,
使人间有一座圣坛,一片净土,
夜莺的鸣啭在这里永不消逝。
“翻译济慈的诗难度很大,不仅要用中文译出原作的韵律、节奏,还要译出原作的神韵,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合一。”屠岸说,自己在翻译时都会反复朗诵原作,用心体会,反复琢磨、推敲,最终才会定稿。他早年在出版社工作,只能业余时间翻译,离休之后,才得以集中时间翻译。有时兴致高,他会连夜译诗,白天睡觉。近年,屠岸又出版了《英国历代诗歌选》上下册,以一人之力译介英国历代152位诗人的580多首诗,这几乎耗费他毕生的精力。
不过,翻译诗歌的稿费很低。屠岸感慨,自己的前辈和同辈翻译家,如王佐良、袁可嘉、查良铮等人,翻译诗歌完全是出于事业心,是为了对诗歌的奉献。相比之下,今天年青一代诗歌翻译家仍有一批,但成就突出者极少。“现在社会太浮躁,翻译没有丰厚的稿酬,发表了也没几块钱,没有人愿意把精力放在这上面。”他无奈地说,年青翻译家一定要有奉献精神,把翻译当作自己的事业来看待,不能当作游戏、小玩意儿。
论创作 口水诗不算诗
屠岸走上诗歌翻译、创作的道路,有其家学渊源。他的母亲曾是常州女子师范学校首届毕业生,古典文学造诣甚高。早年间,屠岸曾翻译出版惠特曼的《鼓声》,则是得益于胞兄的帮助。在家里,他的夫人方谷绣也是一位诗人,夫妻二人经常一起翻译、创作,两人合作翻译出版过英国诗人斯蒂文森的《一个孩子的诗园》,这部儿童诗集在英国家喻户晓。
屠岸的子女也都爱好文学。前几年,他家每周都会举办家庭诗会,“我的三个子女和外孙女、外孙,每周来家里朗诵、研讨诗歌,有中外诗人的诗作,有翻译的作品,也有朋友写的或自己写的作品,古今中外的诗歌都有。诗会名叫‘晨笛’,原是外孙的名字,寓意朝气蓬勃的意思。”屠岸笑道,现在由于人总是到不齐,家庭诗会就停止了。
最近刚出版的《狄金森诗歌选》,收录了美国大诗人狄金森200多首诗歌的译作,这是屠岸和小女儿章燕合作的成果。“章燕现在是北师大外文学院教授,她在大学里也是学英语专业的。我和女儿经常合作,她译一些诗,我来修改、加工,互相探讨怎么翻译会最好。”他坦言,自己岁数大了,原来特别想翻译弥尔顿、济慈更多的诗,现在可能做不到了。国内目前还没有弥尔顿、济慈的中文版全集,在他看来是一件很遗憾的事。
如今,屠岸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,读书看报与翻译、写作各占一半时间。“翻译要有悟性,但可以订计划,每天可以译一点;但创作靠灵感,没有灵感没法写诗,所以创作没法订计划。”他谦逊地说,看到别人的翻译,跟自己的译作比一下,自己不自满但有自信。但对于诗歌创作,屠岸直言自己还缺乏一些天赋。
说起当下诗坛一些怪现状,屠岸语气略有批评。他认为,不管是自由诗还是格律诗,诗歌还是要讲究一点韵律形式感,否则就变成了散文。“现在出现的梨花体、口水诗,还有人提出口号,要颠覆崇高、理性,只想留个名声,但他们的那些作品根本不是诗啊!”在他眼里,中国诗歌是要变化的,但万变不离其宗,这个“宗”就是真善美,离开了这个“宗”,就变成假恶丑了。
人物小传
屠岸,1923年生于江苏常州,本名蒋璧厚。1942年至1946年肄业于上海交通大学。他于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,其译著有《鼓声》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》《济慈诗选》《约翰王》《英国历代诗歌选》等,并著有诗集《屠岸十四行诗》《哑歌人的自白》《深秋有如初春》《夜灯红处课儿诗》等。
绍兴翻译公司推荐阅读